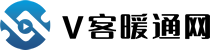“‘暗刺激’这个词有吸引力,但是我认为好像是不存在的。实际上我们的政策措施都是公开透明的。如果从没有透明化的角度理解的话,我认为不存在‘暗刺激’。而‘微刺激’这个词,我认为还是比较能够反映当前我国经济预调、微调、适时适度调节的特点”。
日前,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,在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吹风会时,对当前的我国新宏观调控方式,以及统筹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防风险等方面的情况做出详细介绍。他指出,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虽然还在轻微下行,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是7.4%,比去年的7.7%下降了0.3个百分点,但是依然是运行在平稳增长的区间内,没有脱轨。
他认为,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机遇期尚未消失,增长的动力和因素已经大量释放,但是还有一些潜在的因素要释放,如城镇化深化、工业化深化,特别是中西部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等。消费水平的提升带来城乡居民创造的内需的扩大,而制造业体系形成了,规模扩大了,自然也会扩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。
当前调控属于“微刺激”
陈东琪指出,新一届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总体上保持财政政策积极、货币政策稳定,这个基本趋向没有改变,但是这几年此项政策的稳步实施和推动,并不意味着稳定就是不作为,相反积极就是扩张。如稳定的货币政策,今年3月份以前,M2是下行的,3月份是12.1的增长,广义货币的增长,那么它是一个向下调整。3月份是13.2,增长了一点,这说明我国在金融政策、货币政策操作上保持了弹性,这是一个“微刺激”。
“我们在减税,在对中小企业鼓励创新的政策安排上,也是采取了微调方式,在宏观风险方面的做法也是采取预调,还有在公共设施的项目安排上等方面,都采取了微调的方式,动作不大,不是全面扩张,不是全面刺激,这跟2008年4季度、2009年的政策相比,是有明显变化的,符合现在经济缓慢减速这样一个形势的需要”。
陈东琪继续指出,现在国际形势,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,采取预调、微调,适时适度的这种“微”一点的措施操作,符合现在形势的发展,效果也是比较好的。如果调整动作太大,虽然经济能够很快上去,但有可能为今后经济发展留下后遗症。此外,动作大的话,经济一下子上来,调结构、搞改革就没有了积极性。所以,用这种预调、微调的办法,能留出调结构的空间,留出更多出台改革开放措施的空间,也给企业、给地方政府、给市场主体以主动创新的压力和动力。他认为,如果用“微刺激”代表预调、微调的概念和提法,符合现在的发展需要。
经济还有下行惯性
近日,相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数据,其中4月份的用电量同比增长4.6%,同比下滑2.2%,比一季度又下滑了0.8个百分点。作为经济的晴雨表,对此也有分析人士担心,用电量的下滑可能意味着经济下行的压力继续加大。
陈东琪指出,衡量经济运行趋势的指标有很多,用电指标、供电指标,企业的用电量、普通消费者用电量和电力公司的发电指标等都很重要。此外,还有港口吞吐量指标,企业PM2指标、货币指标,还有狭义、广义货币供应量。除了这些指标以外,还有收入指标、就业指标,等等。
“用电指标在下降,我们也注意到了。港口指标这个月在增加,而且最近几个月在变强,前十大港口吞吐量4月份比3月份出现向上的趋势,上个月是6.5%,4月份是7%。按照汇丰的统计,先行指标中服务业是54,接近55;制造业采购指数这个月比上个月加速了0.1,50.3~50.4;货币指标M1、M2,4月份都在加速,M2是3月份12.1,4月份13.2。M1一月份是最低的,1点几,现在又回了几个百分点”。
“通过这些综合指标来判断,我感觉经济还有下行惯性,压力还没有完全消除,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的下降趋势。但是先行指标开始出现触底的信号。我的基本判断是,二季度经济下行还有一定压力,有一定的惯性;下行过程中运行态势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;在一定时间后,经济可能会比悲观的预期要好一些。因此,中央讲的7.5%的增长目标,按照我的分析,有可能基本实现”。
陈东琪指出,至于当前电力指标的下降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第一,经济总的景气度没有恢复。先行指标好了并不等于总的景气度完全恢复;第二,结构在变化。现在货运量的增长、用电的增长同步都还不太好,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构在渐渐变化。变化之一是产业结构,服务业增长,贡献增加,工业里面的原材料工业、采掘工业、原材料的低加工工业贡献在降低,尤其是重化工业。
而今后随着经济的复苏,无论消费结构、产业结构、供求结构的调整,都是渐进的,经济开始触底回升了,预期好了,全社会用电特别是消费用电、服务用电可能就会上来,所以这两种力量对比的时候,如果这种力量是平的,哪种力量大,可能会往哪个方向走,所以用电指标一段时间以后,可能还会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。
与欧美复苏不同步可能是长期现象
据了解,目前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复苏,但相比欧美,中国的经济却没有明显的好转。陈东琪也承认,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,这两年出现一些新的变化。“去年上半年欧元区欧盟经济还比较差,甚至有的还是负增长,下半年触底回升,今年则出现了同步向上”。
他继续指出,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也存在一个现象,即进口弹性在下降。据介绍,美国经济名义增长3以上,但是它的进口从三年以前的两位数到今年一季度的负增长。原因主要是:美国、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开始再工业化,这样产生对中国出口的挤出效应;美国现在的整个景气度、消费预期比较好,它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增长,如房地产,证券包括债券和股票价格的上升,使他的家庭资产增长效应明显。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,特别是新生代的消费者,虽然现金收入没有增加,工资收入也没有增加多少,但因为房价上涨了、证券股票价格上涨,所以也有消费意愿和行为。
“以前是欧美好,中国更好;欧美平,中国也向上;欧美差,中国差得少一些。现在是欧美上升,中国还在缓慢下行”。据他介绍,除了欧美发达国家进口弹性的系数下降以外,我国经济复苏较慢也有一些自身原因:一是发展模式弊病逐渐显示,特别是在本世纪这15年当中的效果,发挥到了极致。二是需求侧消费者结构在调整,供给侧企业成本在变化,现在企业综合成本竞争力在下降。三是汇率成本增加,2005年7月到现在,9年多的汇率改革,人民币不断升值,总体上增长了30%。累计提高的边际效应就产生了,所以企业突然发现出口困难了,等等。
陈东琪认为,欧美和中国经济这样一个不同步变化现象,这种短期的交叉现象,有可能变成一个中长期问题,这意味着:一个是结构性问题,一个是周期性问题。结构性问题说明我国的发展模式,特别是数量型的出口模式要调整,意味着产业发展模式要调整,原来的低中端,慢慢要向中高端迈进,我国产业发展格局要适应这种全球格局的变化。
微信
日报
抖音

暖通空调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平台

网罗暖通空调行业最前沿资讯

解锁暖通行业更多精彩,“抖”在这里